首页 > 生命线出现月牙
【职烨的《刻在生命线上的故事》】
把所有的心情都摊开来体会
把全部的话都说出来你听
看看还有什么让人担心
不要考虑地太多自己迷惑
世界总是反反复复错错落落地飘去
来不及叹息
生活不是平平淡淡从从容容的东西
不能放弃
——老狼《蓝色理想》
槛槛从箱底把老狼的磁带翻出来给我,我听了,接着哭得一塌糊涂。
然后,我开始插着口袋在街上乱逛,像从前一样。许久以来沉淀在心底的往事一点点地浮上来,浸润到每一寸肌肤,每一缕发梢。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然而当那种排山倒海的感觉卷过来的时候,我蹲在地上,好半天才站起来。
我于是决定把它们都写下来,一点一点,毫无遗漏地,写下来。
我妈妈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我这样说可能不太好,但是这是事实。每个人看到她走在街上,都是忍不住要回头看两眼的。妈妈总是站在镜子前对我说,要不是生你,我哪会像现在这样胖。我觉得她是不喜欢我的。因为我一天天地长大起来的时候,妈妈就不可避免地一天天地衰老下去。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就像我管她叫妈妈而她管我叫女儿一样是无法改变的。从我有印象的时候起,妈妈就一直是迅速地旋进家门,匆忙地换上衣服又一阵风似地旋出去的影子。我从来搞不清楚,她究竟在干些什么,又在忙些什么。妈妈对我而言,就只是一个熟悉的称谓,仅此而已。
后来有一天,我看见一个陌生的男人躺在我们家的床上,哼哼唧唧地发出很奇怪的声音。我吓死了,一个人跑到马路上站了一个下午,晚上回去的时候,我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床上抽烟,花瓶碎了一地。他把我拉过去,“烨烨,你喜欢爸爸吗?”
“喜欢的。”
“喜欢妈妈吗?”
“喜欢的。”
“以后跟爸爸两个人住好吗?”
“妈妈呢?”
“不管她。”
时钟在头顶敲了八下。
那年,我八岁。
我喜欢在路上走
看着太阳
看着她从草尖上
从羚羊的角弯里
从干燥的桔秆上升起
上了小学以后,我开始变得很反常,经常和男孩子们打架打到头破血流被老师送回家让爸爸教育。爸爸一直叹气,我在一边像公鸡一样地抬着头。“烨烨,为什么打架?”
“我讨厌他们。”
“为什么呀?”
“他们踩死了蚂蚁。”
“你是女孩子!”
“可是他们踩死了小蚂蚁的妈妈。”
我一直不愿意承认,我是很在意母亲的。我其实一直希望那个我管她叫妈妈的女人能够重新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一种得不到的痛苦里面,尽管掩饰得很好,但得不到的终究无法得到,痛苦终究无法变成幸福。
我喜欢在路上走
我喜欢在昏黄的路上
看见灯光
我喜欢一个人
一个人
必须有太阳。
初中对我而言,是一个空白。我结束了小学里的荒唐,开始变得循规蹈矩起来。规规矩矩地读书,规规矩矩地生活,规规矩矩地做人。我隐瞒起从前的种种,我是一个好孩子,一个每门功课都拿第一,每天穿干净整洁的校服,梳整整齐齐的马尾辫的好孩子。我的文具盒里的铅笔总是削得尖尖的;我的课本总是平整的包了四个角的书皮的有淡色花纹的那种;我的字总是方方正正一板一眼地贴在格子的正中;我的球鞋总是雪白的;我的笑容总是灿烂的。我瞒着父亲在升学表格的家庭状况一栏填了“和睦、良好”,我凭着优异、优异、全部优异的成绩,直升进了一所市重点高中。
然后,我碰到了槛槛。那是一个长得很亲切的男孩子,很平民化的相貌,但是让我觉得很舒服。槛槛没有爸爸,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太平静了,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他说,那是他们大人的事情,我们小孩子没有必要搅在里面;他说,自己要活得开心一点;他还说,妈妈一个人养大他不容易,不能再让她操心了。我看着他,他的眼睛是咖啡色的,一直可以望到里面去,我一下子觉得好开心,从来没有过的开心。背了很久的包袱,突然有一个人帮你卸下来了,那是怎样的一种舒适与畅快啊。
我跑回家,爸爸正蹲在地上拣菜,我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站着。爸爸然后抬起头来,眼角眉梢的皱纹一道道地杵在那儿。“烨烨,你干嘛?”
“爸爸。”
“嗯?”
“爸爸,我爱你。”我奔过去搂住他,父亲的身躯已经不伟岸了,我甚至可以感觉到他突出的骨骼和松弛的皮肤。我就那样搂着我的父亲,眼前迅速闪过一幕幕的情景:
三岁的时候,我一直生病。经常半夜三更莫名其妙地发起烧来。父亲用毛毯裹着我,在三九的天里,在半夜12点没有车的街上,一脚深一脚浅地找医院给我挂急诊看病。
六岁的时候,父亲骑着我去学手风琴。五十多斤的琴背在背上,自行车上再带个我。我叽哩咕噜地坐在车前的横杆上背新学到的古诗。父亲一低头,硬硬的胡子扎在我嫩嫩的脸上,两个人一起开心地笑。
九岁的时候,我和别人打架,那个小朋友的家长找上门来,父亲边递香烟边陪笑脸,表情很尴尬,“我会好好管教她的。”然后,他坐在门口抽烟,我就远远地站在那儿等着被打。但父亲没有动,一直在抽烟。
十岁的时候,父亲戒烟,并开始兼职替别人修电器,用来补贴家用。我无意中听到姑姑说:“他还不是为了烨子,这么不要命地工作,唉!”
十二岁的有一天,父亲小心翼翼地问我:“烨烨,要不要给你找一个新妈妈?”“你去找,找了你就不是我爸爸!”我的话狠狠地砸过去,随后,重重地摔上门,身后是父亲受伤的眼睛。
十三岁,我开始认真读书。饭桌上不再叽叽喳喳地告诉父亲学校里的事情。父亲每每总是用“最近学习还好吧”开头,再被我用一句“很好”堵回去。
我的眼前迅速地浮上一层水冰蓝色的雾气。我感觉父亲的肩抖了一下。“烨烨,你怎么了?”
“爸爸,你给我找个妈妈吧。”我把头埋在父亲的肩膀上。我怕他看见我眼里亮亮的东西。
后来,我给槛槛写了很长很长的信,告诉他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和我的过去。槛槛给我回了信,很短。他说,“烨子,我喜欢你。”那天,我牵着他的手走回去,走了很久很久,去看了他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再然后,我的爸爸和他的妈妈就走到了一起。他们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竟已学会了槛槛的平静,我说:“好的好的,爸爸,我同意的。祝你幸福。”但我没有叫那个女人“妈妈”,她没有我的妈妈漂亮,我的妈妈只有一个,虽然她不喜欢我。
槛槛于是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我的哥哥,我没有别扭的感觉,一点也没有。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一点做作的意思也找不到。我还是牵着他的手走回去,他用褐色的眸子看着我,他说:“烨子,我喜欢你。”
高二的时候,我给报社寄了稿子,我用一个男孩子的笔调写了一个我曾经幻想的爱情故事。那个故事其实是我构想过无数次的,就如同一个绚烂的水晶遥远地挂在天边。然而当我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水晶破碎的声音,和着早晨校园里清脆的花开的响声,好听地落下来,落到遥不可及的梦里。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是有遗憾的,因为遗憾,我们才生活在一种错过的美丽里。
雨后的青春睡了
天空的早晨醒了
大海的皱纹深了
城市的泪痕浅了
你哭过了,也就算是惦记我了。
妈妈后来有一次回来看我,老了许多,但还是很漂亮。她说她过得不好,她说她想我了。她说:“烨烨,你不要恨我。”我就那样静静地看着那个蹲在我面前轻轻啜泣的女人。她的头发散下来,密密地铺到面前,我看不见她的眼睛。我站起来给她泡了杯菊花茶,淡黄色的花瓣在嫩黄色的清水里舒展开来,一瓣一瓣地好看的漾出去,然后一朵一朵沉到杯底。浅白色的雾气升起来,我用手捂着它们,温暖地泛着湿气的雾气。然而,我的眼眶是干的。当最后一朵菊花优雅地降下去的时候,我笑了,眼睛弯成好看的月牙,我说,妈妈,我不恨你。
我其实从来都没有恨过她。我第一次看见那个男人的时候,我以为我恨她;她抛弃我和爸爸潇洒地离开的时候,我以为我恨她;我在升学表格上填上“家庭和睦”的时候,我以为我恨她。然而,当那个女人卸下雪白的粉饰,略带疲惫地用看不见颜色的眸子望着我的时候,我竟然一点愤怒的意思也没有。菊花一朵朵地沉下去,我知道,一切的一切都过去了。我的略带清涩的童年和反反复复的少年,我的无数个流着苦楚与自卑的眼泪的逝去的日子。既然已经自然地沉下去,又何必不择手段地把它们捞起来,就让它们呆在那儿吧。静静的,很好。
生命里的许多事情,其实都是无法改变的。每个人带着希望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注定要甩不掉一些烙在生命线里的故事。就好像,我管那个女人叫妈妈,不管是从前,亦或是将来。
眼里的星星闪光
梦里的钥匙丢了
心里的翅膀飞倦了
书里的故事走远了
我在这个寒风冽冽的冬日里,在老狼干净、透明、没有杂质的声音里,拾起了一些刻在生命线上的故事。你听见了,也就算歌唱了。
生命线出现月牙相关文章:
-
2023年7月17日扫舍宇怎么样[哪天扫舍宇吉利]
在2023年7月17日这一天,全国各地都庆祝了扫舍宇吉日。这一天,对于人来说非常重要,有许多传统的庆祝方式,让人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气氛。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对2023年7月17日...
精彩资讯 2024-11-10 15:27:25 -
2023年10月6日剃胎发好吗[哪天剃胎发比较好]
剃胎发是一种在传统文化中非常普遍的习俗,一般在孩子满月或百天的时候进行。但是,是否在2023年10月6日剃胎发比较好呢?本文就从五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剃胎发的起源 剃胎发...
精彩资讯 2024-11-10 15:26:58 -
2023年10月27日能离婚吗[离婚吉日查询老黄历]
在老黄历中,2023年10月27日是一个适宜离婚的日子。但是,离婚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需要考虑很多方面。本文从准备工作、财务安排、子女教育、社会压力和情感问题五个方面进行详...
精彩资讯 2024-11-10 15:26:40 -
2023年9月4日封顶好吗[哪天封顶比较好]
2023年9月4日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因为这一天被定为封顶日。关于封顶日的选择,有人认为应该将其定在一个吉祥的日子,比如中秋节或者春节。但是,中秋节和春节是全民欢庆的节日,选...
精彩资讯 2024-11-10 15:26:40 -
兔猴属相合吗,猴女为什么不能嫁兔
属猴女和属兔男是不太相配的一对,因为从十二生肖的角度来看,这两个生肖是相冲的关系,天生不和。兔猴是相害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很难相处的,婚姻生活并不会很顺利。猴和兔属相...
精彩资讯 2024-11-10 15:26:21 -
属猴男和属猪女能过一辈子吗?属猴狮子座从事什么职业好?
属猴狮子座从事什么职业好?十二生肖之中,申猴与亥猪为***,与寅虎、卯兔为三合,与巳蛇为相害,而申猴与亥猪为相冲,故而属猴男和属猪女能过一辈子吗?属猴狮子座从事什么职业好?...
精彩资讯 2024-11-10 15:2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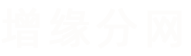 增缘分网
增缘分网![2023年7月17日扫舍宇怎么样[哪天扫舍宇吉利]](ky/data/images/notimg.gif)
![2023年10月6日剃胎发好吗[哪天剃胎发比较好]](http://www.zengyuanfen.com/upload/file/202305/small4f64c9298c5b62168c916a68b010d9481683985306.jpg)
![2023年10月27日能离婚吗[离婚吉日查询老黄历]](http://www.zengyuanfen.com/upload/file/202305/small7b38d43afd36e16091f044c34148eb381683986828.jpg)
![2023年9月4日封顶好吗[哪天封顶比较好]](http://www.zengyuanfen.com/upload/file/202305/smallb1d3a3a4177f96bcb4d7dabcb751a7671683986831.jpg)

